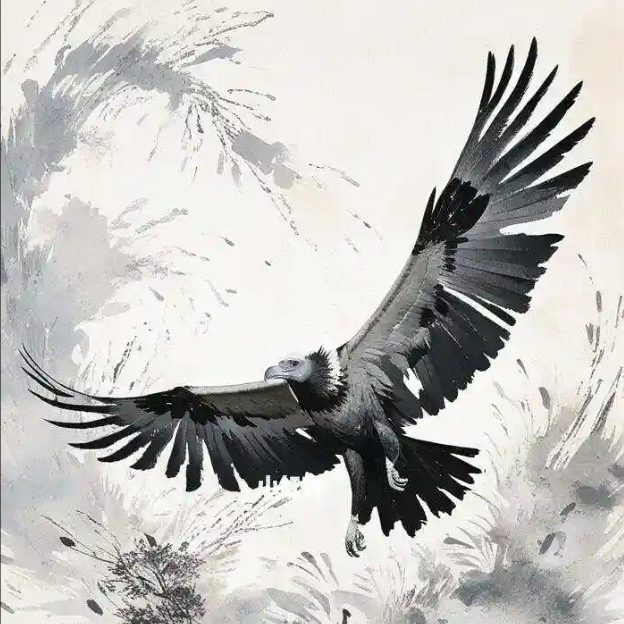旷野还是轨道:我在DNA找到的答案
来自NOII
对于很多人来说,“旷野”与“轨道”既是现实争论也是思维困囿,DNA的第一次圆桌会也是以此作为议题。为大家抛出论题并且主持了圆桌会议的Noiii,在这次圆桌会之后的两个月里,还一直在思考着这个人生哲学问题。
▷ 「究竟什么样的生活算是“旷野”,⼜该如何下定决⼼⾛出原先的“轨道”?跃⼊旷野之后,是否找到了更开阔的人生?」
看到《⼈物》这篇征稿的时候,我刚从欧洲交换回来,下定决⼼要挣脱既定的主流叙事规训。放弃了秋招,跑去星巴克打了三个⽉的⼯,开始“不学⽆术”地学调酒、学架⼦⿎,试图给⾃⼰留⼀个探索的出⼝。那段时间⾥,我逐渐想明⽩了⾃我存在的意义:不确定性太多,我随时都可能会死。那么我所存在的当下,我正在⾯对的每⼀分每⼀秒,就是我需要⽤⼒活着、向死而生的倒计时。
跃⼊旷野之后,我来到DNA
我给⾃⼰的⼈⽣⽅向定义为存在主义式的「体验」:尽可能丰盈的⽣命体验。我认为我找到了属于⾃⼰ 的“旷野”。
然后我来到了DNA。
和⼤伙吃的第⼀顿⽕锅局上,我第⼀次当众说出所有的思考、反叛与出逃。那些过去让我惴惴不安的声⾳,那些被星巴克店⻓、被不明所以的朋友、被我家⼈反复问起的「你为什么要去星巴克打⼯?」「你为什么不秋招?」,并没有如我意想般地来到。⽽是换之以接纳、了然、共鸣,和很多句的「我也是」。
⾃那天起,我便不断地被DNAer之间所流淌的强连接与共识所打动,这种联结是如此的浪漫恣意且具有⼒量。到现在我都记得,那天出游,阳光下,⻛铃声起,德⽼师的声⾳在不远处回响:「⼀个社区/公社,理应是有些共同理想存在的……」 我要把它拍出来。我⼼底也响起这样⼀个声⾳。
' fill='%23FFFFFF'%3E%3Crect x='249' y='126' width='1' height='1'%3E%3C/rect%3E%3C/g%3E%3C/g%3E%3C/svg%3E)
于是我带着设备再次回到DNA,打算拍条纪录短片。为了拍摄,我又想起了《人物》的征稿,顺势主持了一次圆桌讨论:
「逃离之后,人生是旷野还是轨道?」
但在与大家的交谈中,我发现旷野的叙事并不足以引起广泛共鸣。游民群体实际的身份认同或人生哲学,实则呈现出更为多元的光谱。有理想主义者、浪漫主义者,也有现实主义者、机会主义者。就像我最初所捕捉到的那份出逃的确幸与浪漫,未必能囊括这样一个社区完整的有机生态。
起初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要拍,想拍什么。我发现我逐渐找不到方向了。做纪录片导演的大宝告诉我需要找到一条主线,我说我想拍出一种共性。但“真的存在吗”,十笔那天这么问我。我答不上来。就像是在圆桌那天不少人所指出的,旷野并非想象的那般美好,或者说它从来就不是舒适、安全、自由的指涉。你需要面对的是脱离主流的传统路径依赖之后,回归原始丛林的未知危险与不安全感。陈菲说,所谓的旷野或许只是一次的相对变轨,或许从来就不存在「出逃」。
' fill='%23FFFFFF'%3E%3Crect x='249' y='126' width='1' height='1'%3E%3C/rect%3E%3C/g%3E%3C/g%3E%3C/svg%3E)
△DNA第一次圆桌讨论
我短暂地陷入了一种迷茫。拍摄的计划也暂时搁置了。那是我对旷野想象的第一次脱节。但我没有多想,我始终认为能够觉察并主动悖离主流框架与社会规训已经是非常勇敢的尝试了。
那些日子里,我们一起在冬日的篝火边围炉夜话、在暮色的田野里放飞孔明灯、在稀疏的农田边爬大树听摇滚、在凌晨3点半的小瓦尔登湖发疯蹦野迪……在自然天地间回响震荡的生命体验,让我得以用力呼吸着旷野上每一分秒畅快自由的气息。那是我最快乐的时光。
' fill='%23FFFFFF'%3E%3Crect x='249' y='126' width='1' height='1'%3E%3C/rect%3E%3C/g%3E%3C/g%3E%3C/svg%3E)
' fill='%23FFFFFF'%3E%3Crect x='249' y='126' width='1' height='1'%3E%3C/rect%3E%3C/g%3E%3C/g%3E%3C/svg%3E)
后来3月初,周五老师来上海,我们组了个DNA临时分队,一起喝了点酒,聊了点在DNA习以为常的天。突然就意识到,在场的人多数都回到了原有的轨道上。于他们而言,DNA是一场梦,一个乌托邦,一种寄托美好情感的符号。离开DNA后,似乎又会被原有轨道的一切所吞噬淹没。
「DNA是一个让我短暂逃离的地方,在那里我不用想什么事情,哪怕浪费时间也可以无所谓。」
「但一回到上海,人一下就会变得非常焦虑。」
我隐隐有些不安,这样的时刻早晚会朝我袭来。
' fill='%23FFFFFF'%3E%3Crect x='249' y='126' width='1' height='1'%3E%3C/rect%3E%3C/g%3E%3C/g%3E%3C/svg%3E)
△DNA上海小分队集结
假象之外,真正的“旷野”
果然,很快我便被原有体制的一切拉扯了回去。
当我逐渐回归到家庭、学校、社会的体系下,开始面临毕业的一切琐碎的流程,我不得不去面对那些声量逐日加大的询问、打探、质疑的声音。坚不可摧的社会规则再次一点点将我拉回现实。所有的解释、拉扯、证明,压得我胸闷,我变得焦虑、痛苦甚至一度崩溃。出逃的结果并非我所想象的,可以一蹴而就的纵身一跃。
我又想到了《人物》的征稿,以及在此之后很长时间内被我忽视的那篇回信。
「如果旷野是假象呢?」
我开始重新反问我自己:我的选择,所谓的跃入旷野,究竟是在逃避那些内卷、虚无、艰难的现实,还是真正在孤勇的出逃中重新找寻自我?或者说这样的选择,究竟是旷野还是另一道围城、另一条轨道?
人依然是活在社会与关系中的动物。我既无法全然脱离主流叙事的隐形规范,也无法忽视收入结构的现实难题。或者说我至少需要一个具体的抓手,来应对这套体系规则。与此同时,我也逐渐发现我所自以为的“旷野”变得过于宽阔,它就像是另一种肯定性话语的陷阱,促成了新的困惑:如果是为了追求多元的生命体验,可环顾四周又有太多的可能性,我究竟该向何处出发。我的passion在何方,我该如何寻找?
十笔说这是种诅咒:一旦你开始发问,你就必须要找到答案。
我开始思考,还会有别的解法吗?
' fill='%23FFFFFF'%3E%3Crect x='249' y='126' width='1' height='1'%3E%3C/rect%3E%3C/g%3E%3C/g%3E%3C/svg%3E)
△那天,我们坐在大树上听摇滚
或许,我们都陷入了“旷野”和“轨道”这一伪对立命题的误区。
在互联网语境和媒体泛叙事中,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对旷野和轨道的话语定义好像都在渐渐窄化。对人生选择多样性的呼吁偏离到了对职业类别的二元区分:轨道是枯燥乏味的体制内、996的内卷大厂、固定职业,而旷野就一定意味着灵活流动的自由职业、裸辞旅居、自媒体博主。但其实我们所需要祛魅的假象,是不再迷信与盲从那份一定指涉自由/躺平的旷野想象。而我们所深感迷茫的,或许也并不是选择朝九晚五还是自由职业的非黑即白,而是内心真正想要探寻并向往的,那个让自我最具有意义感的方向与理想。
因此,比起说跃入旷野是一种一时冲动逃避现实的假象,不如说我们所需要呼唤的,是一种对单向度的社会时钟和主流规训的觉察。觉察/看见本身便是一种力量,也唯有从觉察开始,我们才能从功绩「轨道」下内卷剥削的集体无意识中觉醒,从只能“理性地、有生产力地生活和死亡”的被动顺从中挣脱,继而唤醒内心深处隐匿已久的否定性力量:首先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的主体性。
诚然在这样狭隘的话语语境中谈「旷野」,本身就是极易使人混淆方向的事。但我仍然想保留这一话语的原因在于,所谓「旷野」,比起与「轨道」相对的物理自由的隐喻,它不仅在于摆脱强制与纪律的否定,更在于心灵上的真正自由。那是在觉察既往被建构的、被规训的、被异化的“单向度”自由之后,所自然向往的人生意义所在,是真实的人生需求,是真正想做的事,是个体对自主时间的追求和对自我生命意义的叩问。这个来自你内心的声音,可以是自由职业意义上的旷野,也可以是变轨到另一条轨道,甚至可以是重新回到原有的那条轨道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真正的「旷野」,理应是脱离外界定义向度、符合个体内心真实向度的存在之地。
' fill='%23FFFFFF'%3E%3Crect x='249' y='126' width='1' height='1'%3E%3C/rect%3E%3C/g%3E%3C/g%3E%3C/svg%3E)
△我们的翻墙爬树四人组
当然可能也如我在大理遇到的一位朋友所说,比起理论世界的理想化,现实生活更多是意义与狗屎的部分混杂难分。比起对异化的现代工作制全然否定,和自我剥削的消费主义倦怠社会迎面对击,与毛细血管般的权力规训揭竿相抗,我们更多时候处于一种更为复杂的动态博弈之中:一心追求内心的自由,却又始终被庞大的体制与系统所拉扯。我们确实无法一劳永逸地找到真正的自由,但私以为只有知道了不想要什么,学会将目光从外界的声音抽回,或许才能更好地将目光投向内心真正想要的「旷野」。
依稀记得那次圆桌时,周五说他一直在找能够为之投入一生的事业,但还没找到,他决定在DNA再等等。我彼时不解,“真的能找到吗”又或者“真的存在吗”。
但今天我也站在了同样的境况中。我需要一个目标感,我想要去寻觅。
上海706的Lee说,逃离轨道/跃入旷野的人中,有人痛苦地回到原有轨道的安全区,有人选择留在未知的旷野。而留下来的人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亚比群体中的“糊比”人群,在大理有很多。他们安于停留在原地的现状,在虚无中达到自洽,就好比现在的“淡人”。另一类是像我们一样,在社区中会遇到的青年群体,逃离主流叙事来到旷野之后,既不甘于停在原地,却又环顾四周,找不到前进的方向。这是他为什么要做青年社区的原因:试图提供一种可能性。
这句话突然就点醒了我。我一直在寻找的共性是什么。
或许答案就存在于DNA,在社区之中。
回到社区,在波西米亚主义的集体生活叙事中寻找答案
本雅明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中重新描绘了一类反传统的、浪荡漂泊的「波西米亚人」。他将波西米亚人的形象定位于一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抵抗和批判,这种抵抗和批判体现在他们对都市生活的漫游、对商品文化的反思以及对个人身份的探索上。
现代社会的波西米亚人,好比游离在现代性规范范畴之外的都市游荡者。他们居于人群中,不断巡逛与张望。周五说他的微信名「三亩田浪荡子」正是源于此。holi则将在DNA的生活形容为「乡村游荡」。而无论各种游荡,都不仅仅是物理上的移动,更是精神上的游历和探索,这与个体跃入旷野的叙事语境无疑是相似的。
然而波西米亚人从来不是孤立的一个人,它可以是一个人群。或许它也并非一定要是人,它可以是一个地方,一个社区,可以是一种集体性的崭新生活叙事。
据维基百科,波西米亚主义(Bohemianism)是指称那些希望过非传统生活风格的一群艺术家、作家与任何对传统不抱持幻想的人的一种生活方式。
而DNA这样的社区在重构的附近之外,更能成为这样一个可以承载「波西米亚主义的集体生活叙事」的地方,一个帮助个体重拾主体性、找回答案的空间载体。
' fill='%23FFFFFF'%3E%3Crect x='249' y='126' width='1' height='1'%3E%3C/rect%3E%3C/g%3E%3C/g%3E%3C/svg%3E)
△元宵节放飞孔明灯
首先,波西米亚主义天然就带有高度的流动性。而集体流动的社区人员与长期开放的环境,实则更能将个人置于创造自身生活环境的中心,以激发人的自我内观、觉察与表达,不断探索自己的极限和能力。学界对流动性的普遍阐释正是游民能够在社区环境,在与各种人的链接中更清晰地构建自我身份认同。
你是谁,你是做什么的,你想做什么,你为什么来到这里。这样的发问发生在社区的无数个瞬间,在无数的人之间交互。某种程度上,人已经被动或下意识地完成了对自我的多次拷问与沉思。如此高强度的自我觉察与自我思考,是只有在这样脱离原有固定圈层的流动且多元的社区环境中方可激发出的。
就像我第一次在火锅局上说出自己的想法时,在宿舍夜谈面对真真的疑问时,在拍摄时被数次问到的创作表达时,在深夜的小巨蛋被问起未来选择时……回想起在社区中展开的每一次随机谈话,有些短到几句招呼就结束了,有些长到几个小时也孜孜不倦,有匆匆相识的遗憾也有彻夜长谈的深思。有时候也不说话,就是静静地待着,看着远方发呆。但正是这些无数次打破固有气泡,与人和世界联结的瞬间,都让我猛然认知到很多从未思考过的自我切面。
同时在社区的流动性之下,则是多元多样的职业背景与个人视角,这让个体自我身份的构建得以拥抱更广阔的可能性与包容度。在无数个反观自我的过程中,我也得以于众多的DNAer身上发现了更多的可能性。有人从过去的泥沼中挣扎着爬起,有人经历短暂的驻足与困惑后重新整顿出发,有人早早地找到理想的灯塔全心奋斗,也有人在每个当下的时刻感知世界与自我,有人抛下世俗成见选择回归本真……那是在灰色的标准化现代社会难以看到的五彩光谱。因此比起跃入所谓非主流的旷野,倒不如说,DNA的旷野,是比主流社会具有更多样职业选择与更包容文化环境的理想空间与次级群体。每个人在社区中都能找到自己的答案与可能性。
' fill='%23FFFFFF'%3E%3Crect x='249' y='126' width='1' height='1'%3E%3C/rect%3E%3C/g%3E%3C/g%3E%3C/svg%3E)
△百鬼夜行那夜,我们爬上了茶山的旷野
其次,集体性的波西米亚主义极易建立高度凝结的情感联结与理想共识,即逃离现代性异化的普遍初衷与对自我叙事的阶段性追寻,而在这一共识基础上所构建的情感网络则易导向更为紧密的强连接共鸣,从而甚至有可能构成一种关系性的社区集体“共鸣”。
在社区中随机建立起的关系链接是件非常奇妙的事。就像我到达DNA的第一晚,我们围坐在大厅的炉边烤火。柴木在火焰中静静燃烧,炉边的一圈橘子和红薯被烤得发红,手捧一杯热茶翻动着手心手背。那是一种独特的氛围,一群人闲聊着,我没来由地就接过了话头,加入聊天,像是认识已久的好友。
就像我从未想过自己会继而与一群人建立如此长期且紧密的链接。认识了许多契合的新朋友,也与「竹林?闲」的好朋友们相遇。从起初的5人到现在的11人,那是哪怕离开了固定的地理位置与属地空间,也能够随时共享情感与想法的亲密关系。就像是重现了汉德克与韩炳哲所畅想的“根本性的倦怠”,它取消了孤立的主体,产生了一种无需亲缘关系的集体社群,一种无需任何家族的、功能性的纽带。
“在我的记忆中,我们总是在下午的阳光里坐着,交谈或沉默,享受共同的倦怠……一片慵懒的云朵,一种超越尘世的困倦将我们彼此联结在一起。”
而当我们将断裂、疏离、碎片化、异化的自我与周围的同质个体重新联系起来,心中的“旷野”究竟在何方可能不会立即有答案,但至少会重新拥有一份摔倒了也会被轻轻托住的笃定与安定,或许还有越来越明亮的前方。
' fill='%23FFFFFF'%3E%3Crect x='249' y='126' width='1' height='1'%3E%3C/rect%3E%3C/g%3E%3C/g%3E%3C/svg%3E)
总而言之,**提出波西米亚主义的集体生活叙事,是意图呼吁一种或弥散或凝聚的结构性力量,为个体在旷野中的孤独之旅提供足以产生微小震颤的社会支持。**它可以是共同体,可以是重构的“附近”文化,可以是回归交往理性的公共空间,可以是“异托邦”的社会空间,可以是现代意义的“阈限空间”。也可以仅是来来往往的人有机地聚合在一起,用流动的集体生活叙事为彼此搭建缠绕交织的“社交生命线”,共同呼唤一种开放、平等、共享、自由、协作的理想精神,并期冀能在个体孤立的漫游之外,提供一种对异化与规训进行意向性抵抗的集体实践。
同时对个体而言,我们依然可以做探险家,游荡者,波西米亚人,在协商与回击的路上寻找属于自己的叙事,跑向内心向度的旷野也好,书写旷野与轨道之外的第三种个人史也好,继续在DNA这样的日常生活方式之下构建我们的个体实践。
这或许也会是韩炳哲在《倦怠社会》中所呼吁的“一种新的生活形式,由此产生一个新时代、一种新的生命状态,把我们从飞转的停滞状态中解救出来。”
' fill='%23FFFFFF'%3E%3Crect x='249' y='126' width='1' height='1'%3E%3C/rect%3E%3C/g%3E%3C/g%3E%3C/svg%3E)
写到这里,发觉自己又重新拥有了新的勇气和力量。尽管那个方向仍然朦胧未明,但我不再不安。
想起阿伦特在《人的境况》前言中提到的,由于人类公共世界的丧失,无思想是“我们时代的一个最显著特征”,而大声思考我们正在做什么的目的便是在他人身上激起思考。
思考「旷野」与「轨道」这样的伪命题有意义吗?我想或许吧。至少会大声点。
祝我们都能找到自己的答案。